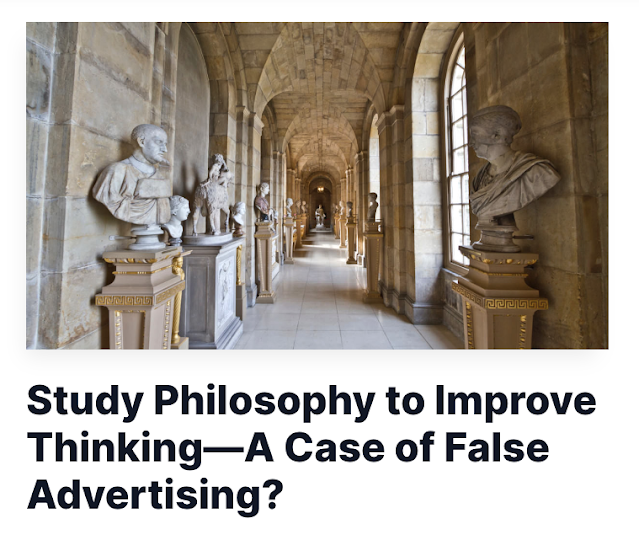如果要問我,作為一個(截至目前為止依舊在象牙塔裡討生活的)所謂的專業哲學家,最討厭被問的問題,又或者是被貼的標籤是什麼,我大概會說是「讀哲學是不是會讓人變聰明阿?」、「你這麼聰明,一定是因為你讀哲學」
這問題讓我非常厭惡是因為,「變聰明」這種問題,如果我們講的是思考速度上升、思考的問題難度加深,這應該要問心理學家、教育學家。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做實驗,去檢驗到底學哲學之前跟學哲學之後,到底在這些層面上有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很遺憾的,目前全世界大部分的哲學系連t-test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做、要怎麼做,都沒有教,更遑論更細緻的統計實驗方法。我會對此略知一二,單純是因為我有修過心理系的統計與實驗課程,與我的哲學訓練毫無關連。
我對這個問題感到厭惡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背後的預設——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可以提供其他學科無法提供的思考訓練,讓人思考的更深入。如果今天我們談的思考的更深入,是哲學中的經典課題,像是自由意志存不存在、到底所謂的「我知道X」是什麼意思、道德義務究竟是什麼,那我部分同意,哲學有其特殊之處,可以幫助人在某些課題尚有更深入的思考。但這就跟歷史系的歐洲中古史會教授其實封建體系(feudalism)是後人創造出來的詞彙,根據學者考證,feudal這個形容詞其實17世紀才出現feudalism甚至是19世紀才造出來的詞,到底中古時代的附庸(vassals)與領主(lords)的關係為何、怎麼互動,其實還需要更深入發掘。用一樣的論述,我可以進一步在把例子換成化學、物理學、數學等等的領域,也就是說,在「可以提供其他學科無法提供的思考訓練」這點上,每個學科都是如此,哲學一點特殊之處也沒有。
如果說,「可以提供其他學科無法提供的思考訓練」指的是「更具批判性的思考」,那我必須說,首先,我根本不大瞭解,什麼叫做「更具批判性的思考」。善意的猜測,所謂「更具批判性的思考」,大概是指更能找到思考、推論間的謬誤等等的。如果如我所猜測,那我必須說,這還是需要透過做實驗才能證明,這不該問哲學家。如果不做實驗,要我按照我自身觀察到的現象來回答的話,我只能很抱歉地說,依我的觀察,很多念哲學的人並沒有展現這些能力。就以我轉貼的這篇文章舉的例子來說:「很多大學讀哲學系的人在GRE、LAST考試分數很高,所以讀哲學可以讓人變聰明」,首先,我們有的經驗證據是「分數高」,不是「變聰明」,這兩邊談的是不同的東西。其次,大學最初級的統計都會教「兩個事件相伴隨發生並不一定表示這兩個事件間有因果關係」,每年的X月X號吃生日蛋糕,每吃一次蛋糕,我就老了一歲,難道蛋糕有個魔力,導致我老一歲?但很多鼓吹念哲學對思考有幫助的人,卻沒有注意到自己地說法其實跟吃蛋糕導致老一歲一樣荒謬。我觀察到的思考謬誤,並不限於此,還有像是只要看到一點「滑坡」就說「謬誤」的這種奇異的「批判」。
真的要我猜一猜,為什麼哲學系學生在GRE跟LAST的成績好的話,那我會這樣猜,第一,在美國,想要念哲學研究所要考GRE,只有少部分哲學所不要求GRE,而且江湖傳聞GRE分數很重要,所以分數要考高,如果是念數學、生物的研究所,就我所知GRE的字彙部分隨便考也沒關係,根本沒人在乎(有趣的是,根據Duke哲學系公佈的資料,他們收的學生在GRE的數學部分平均成績是157,台灣人的GRE成績在這部分,大部分都可以考170滿分,我可以就此推論台灣人平均而言,比duke哲研所的學生聰明嗎?)。第二,美國的教育體制中,大學階段沒有醫學系跟法律系,那都是到研究所階段才有的,所以大學時要找別的系去讀,之後才能申請醫學院、法學院,很多本來就是想要念法學院的人的很可能就這樣選了哲學系當中途之家(有些哲學系有法律哲學系的師資,許多倫理問題、如何認定因果關係等等的課題,也與法律實務算是有所相關)。也就是說,我會猜,考試成績與大學主修哲學間的相關性來源,其實是selection bias,一開始選到的樣本就偏誤了。那些對哲學研究所、法學院沒興趣的學生去考GRE或是LAST,我猜,大概分數也不會很好看吧。但,這都是猜。但我提出的猜測,還是比讀了哲學有如吃了撒尿牛丸一樣讓人好聰明好棒棒來的好吧?
如果念哲學不能讓人變聰明,那念哲學幹嘛?念身體健康不行嗎?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