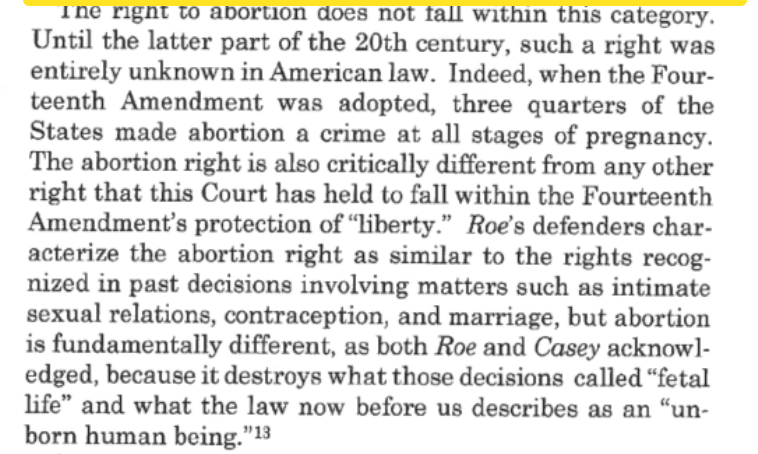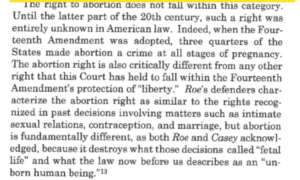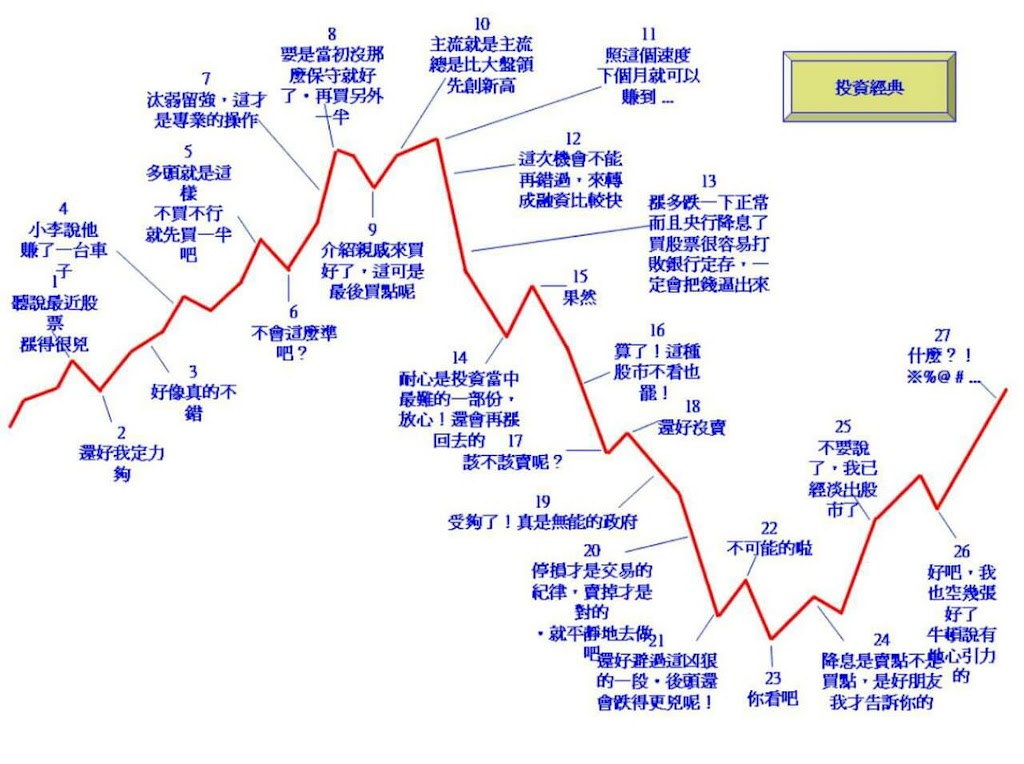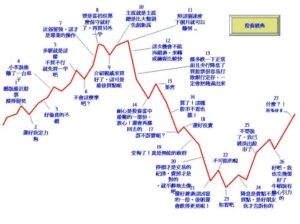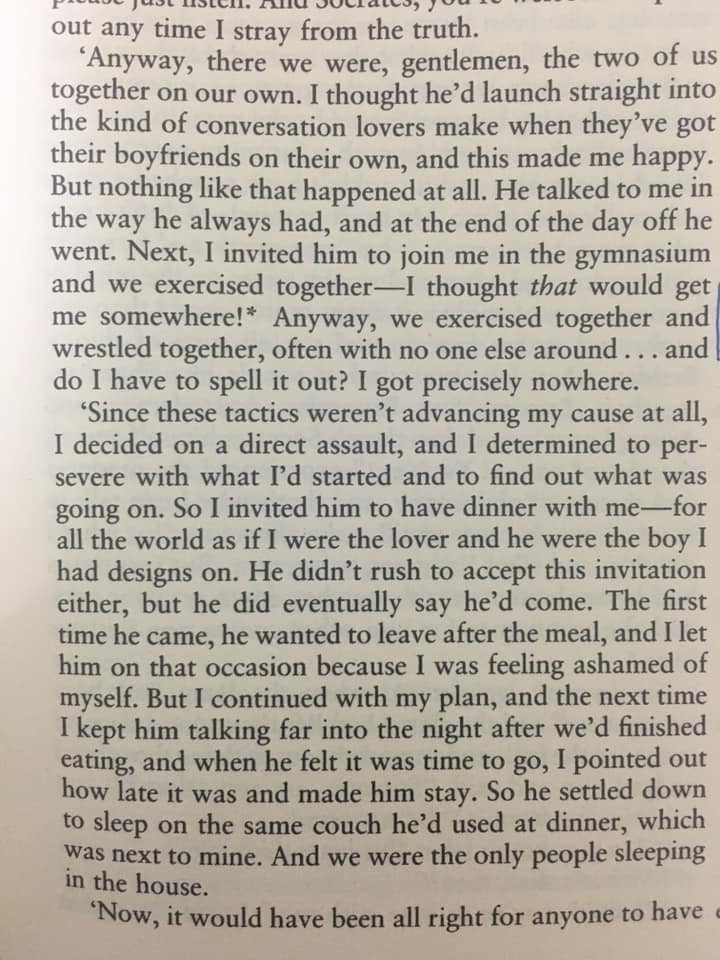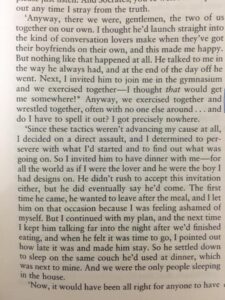最近因緣聚會之下,意外獲得了一本免費的利維坦中譯本(朱敏章譯/商務出版)。本來只是擺在書桌上沒有特別想要去翻動的意思,但見這本中譯本的頁數(296頁)遠低於我手上的牛津編輯過的版本(不含導讀與引索也有475頁),便好奇了起來這本中譯本是抽譯了哪些篇章。
一翻才發現,這個中譯本,某意義上確實是抽譯,只是不是我以為的那種抽譯…
以知名的第十三章on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as concerning their felicity and misery來說,第二段的setting aside the arts grounded upon words, and especially that skill of proceeding upon general and infallible rules, called science 只翻出了science的部分,譯作「但於此須將科學之技能除外」。後面的第四十三章on what is necessary for a man’s reception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也是從第一段開始,就有無數漏譯though it be the command even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whether a monarch or a sovereign assembly) or the command of his father 翻作「則其他縱係君父之命」,whether a monarch or a sovereign assembly完全略過。難怪這個中譯本可以打破我對譯本通常會比較厚的認知,只有不到三百頁。
除了「抽譯」的問題之外,第十三章的開頭兩段的翻譯也有許多微妙之處for prudence is but experience被譯作「蓋人之精明,由於經驗」、That which may perhaps make such equality incredible, is but a vain conceit of one’s own wisdom的That which may perhaps make such equality incredible被翻成了「人之所以為至於他人者」(incredible!!!),而後面的but a vain conceit of one’s own wisdom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會翻譯成「實為一種自滿的假設」conceit是excessive pride in oneself,翻成妄尊自大才比較正確吧,到底何來的假設呢?
倒不是說,我認為這個譯本毫無可取之處,單就文字流暢度來說,這個中文譯本比起現在坊間常見的中皮英骨要來得好得多,如果不是我為人惡劣,把原文拿在旁邊對著看,我不會發現這些問題。但,這個,我不會發現這些問題,就是問題。
—
Hobbes寫的雖然是英文,但他的英文句構還是受到許多拉丁文的影響,對現代讀者來說不是那麼好懂,許多的片語現在也比較少見了。推薦有興趣想要好好讀讀Hobbes的朋友考慮考慮參照著前劍橋教授Jonathan Bennett放在他的網站”Early Modern Texts”上的「英英」譯本,一邊讀Hobbes,一邊也可以學學Bennett的英文,一舉數得。